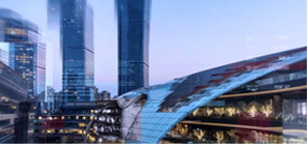對于數(shù)據(jù)業(yè)者而言,數(shù)據(jù)治理(data governance)并不陌生。
根據(jù)國際標準化組織IT服務(wù)管理與IT治理分技術(shù)委員會、國際數(shù)據(jù)治理研究所(DGI)、IBM數(shù)據(jù)治理委員會(IBM DG Council)等機構(gòu)的觀點,數(shù)據(jù)治理意指建立在數(shù)據(jù)存儲、訪問、驗證、保護和使用之上的一系列程序、標準、角色和指標,以期通過持續(xù)的評估、指導和監(jiān)督,確保負有成效且高效的數(shù)據(jù)利用,實現(xiàn)企業(yè)價值。
盡管已將數(shù)據(jù)質(zhì)量管理、數(shù)據(jù)安全管理、元數(shù)據(jù)管理、主數(shù)據(jù)管理、數(shù)據(jù)生命周期管理、數(shù)據(jù)應(yīng)用創(chuàng)新等豐富多姿的內(nèi)容囊括殆盡,但既有的數(shù)據(jù)治理仍然小覷了“數(shù)據(jù)”,并誤讀了“治理”。
數(shù)據(jù)不僅僅是企業(yè)的投入品,更是國家經(jīng)濟運行機制和國家治理能力的“基礎(chǔ)性戰(zhàn)略資源”,其重要性甚至居于礦藏、土地、河流等耳熟能詳?shù)膽?zhàn)略資源之上;
數(shù)據(jù)亦不僅僅是企業(yè)的產(chǎn)出品,更關(guān)乎世界范圍內(nèi)的生產(chǎn)、流通、分配、消費活動,具有全球化和跨國界的天然屬性;
數(shù)據(jù)也不僅僅限于企業(yè),在數(shù)字化生存的時代,它改變了普羅大眾對自我和對隱私的觀念,同時塑造了人與人交往的方式。
以此觀之,既有的數(shù)據(jù)治理掛一漏萬,只看到了數(shù)據(jù)的技術(shù)經(jīng)濟維度,而忽略了數(shù)據(jù)所蘊含的社會性、政治性和國際性的多重面向。
同樣,治理并非公司管理的一部分,相反,它始終關(guān)注著公共領(lǐng)域,并力圖跨越私營部門和公共機構(gòu)的二元對峙,最終實現(xiàn)“善治”(good governance)。
1995年,聯(lián)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在《我們的全球伙伴關(guān)系》中,將“治理”界定為各種公共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gòu)管理其共同事務(wù)的諸多方式之總和,一種使相互沖突的利益得以調(diào)和并采取聯(lián)合行動的持續(xù)過程。
從“管理”到“治理”,在主體上體現(xiàn)為從“單一主體”向“多元社會經(jīng)濟組織”的轉(zhuǎn)變,在規(guī)則上體現(xiàn)為“正式制度”向“契約、行業(yè)標準、其他非正式制度”的轉(zhuǎn)變,在向度上體現(xiàn)為從“自上而下”控制向“自上而下或平行運行”協(xié)調(diào)的轉(zhuǎn)變。
倘若如此思考“數(shù)據(jù)”和“治理”,我們就能在開放的視野中重新定義“數(shù)據(jù)治理”——它不再是企業(yè)價值最大化的工具,而是在數(shù)據(jù)利益攸關(guān)者之間鑄就相互依賴關(guān)系、發(fā)掘數(shù)據(jù)自身價值的基礎(chǔ)性架構(gòu)。
為此,這一新的“數(shù)字治理”可以進一步分解為四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議題:
(1)數(shù)據(jù)治理的目的為何?
(2)誰來治理數(shù)據(jù)?
(3)采取何種方式進行治理?
(4)治理活動受到何種限制?
首先,數(shù)據(jù)治理以“數(shù)據(jù)效率”(Data Efficiency)和“數(shù)據(jù)正義”(Data Justice)為依歸,前者要求盡可能促進各方協(xié)作、減少實質(zhì)限制、制定缺省規(guī)則、降低交易成本;后者主張透明而負責的數(shù)據(jù)處理、設(shè)立高標準的信義義務(wù)、保護弱勢一方并防范數(shù)據(jù)歧視。
如果說數(shù)據(jù)效率是數(shù)字經(jīng)濟滾滾向前的驅(qū)動力,那么數(shù)據(jù)正義就是數(shù)字社會的制動器,兩者的沖突不可避免,因而問題的關(guān)鍵不在于如何取舍,而在于如何平衡。
其次,在去中心化的數(shù)字治理架構(gòu)下,所有的利益攸關(guān)者都是、且應(yīng)當是數(shù)據(jù)治理的主體,這其中既包括了個人數(shù)據(jù)主體,也包括了開展數(shù)據(jù)收集、利用、加工、傳輸活動的數(shù)據(jù)業(yè)者;既包括了對數(shù)據(jù)收集、存儲、利用和公開負有法定義務(wù)的政府機關(guān),也包括了相應(yīng)的監(jiān)督管理機構(gòu);既包括了形色各異的組織體,也包括了組織體內(nèi)部直接從事數(shù)據(jù)處理的組織成員;既包括了本國政府,也包括其他主權(quán)國家和國際組織。
紛繁蕪雜的治理主體迫使我們重思“多利益攸關(guān)方治理”和“網(wǎng)絡(luò)化治理”(Network Governance)的可能性。
再次,治理方式因治理主體的不同而不同:個人數(shù)據(jù)主體享有各種權(quán)利,法定機關(guān)享有權(quán)力,監(jiān)管機構(gòu)擁有特權(quán),而數(shù)據(jù)業(yè)者和其成員不但有著法定權(quán)利,也憑借信息不對稱和技術(shù)能力獲得事實上的控制權(quán)。治理方式的復雜性為數(shù)據(jù)治理開啟了實證研究的視角。
最后,數(shù)據(jù)治理并非在真空中開展,任何治理主體的治理活動均受制于美國法學家Lawrence Lessig所描繪的四種力量,即法律、社會規(guī)范、市場和代碼。
當然,事變時移,這里的“法律”不再由單一國家主宰,而演化為彼此競爭的主權(quán)之中的國家法以及正在成型的國際法;“社會規(guī)范”也因多元的利益和價值而日趨分裂:數(shù)據(jù)自由還是數(shù)據(jù)安全?隱私保護還是生活便利?正如我們的社會一樣,社會規(guī)范正在被打破和重塑;“市場”日趨發(fā)達,但卻遭遇到平臺壟斷和數(shù)據(jù)壟斷的迷霧;“代碼”依然強大,可更強大的算法及其帶來的黑箱卻更令人憂慮。顯然,不斷變化的四種力量劃定了數(shù)據(jù)治理的邊界。
最后必須指出,放寬視野之后的數(shù)據(jù)治理并不是抽象的宏大敘事,而是進行制度比較和問題剖析的宏觀背景。它是起點,而非終點;是開放平臺;而非封閉領(lǐng)土;它遠未定型。
(部分內(nèi)容來源網(wǎng)絡(luò),如有侵權(quán)請聯(lián)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