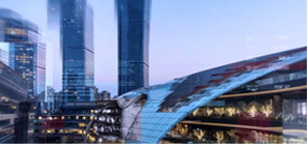? ? ? ?摘要:數(shù)據(jù)時(shí)代,公法學(xué)研究的國(guó)家概念陷入危機(jī)。國(guó)家概念的數(shù)據(jù)化包括前后遞進(jìn)的兩個(gè)步驟:其一是國(guó)家的數(shù)據(jù)化,其二是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形成。在數(shù)據(jù)時(shí)代,作為國(guó)家三要素的領(lǐng)土、人口和主權(quán)概念發(fā)生了實(shí)質(zhì)性變化,主權(quán)國(guó)家的概念喪失物質(zhì)性基礎(chǔ),國(guó)家被數(shù)據(jù)化并呈現(xiàn)為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秩序形態(tài)。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權(quán)力是算力與數(shù)據(jù)的整合能力與控制力。立法者作為規(guī)范輸出的生產(chǎn)者以及讓規(guī)范得以實(shí)施的執(zhí)行者,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可能立法者是作為匿名利維坦的資本、作為技術(shù)自動(dòng)化的人工智能以及作為政治空間的人類自主性。以此,以人之尊嚴(yán)為目標(biāo)的公法學(xué)研究要以人的數(shù)據(jù)化和數(shù)據(jù)的人化為基礎(chǔ),思索秩序與人的自主性同時(shí)成立的可能性與條件,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公法研究應(yīng)當(dāng)回應(yīng)這些難題。
? ? ? ?關(guān)鍵詞:數(shù)據(jù)權(quán)力 數(shù)據(jù)國(guó)家 立法者 資本 技術(shù) 自主性
? ? ? ?引言:“凡可聯(lián)接的,都要聯(lián)網(wǎng);凡可收集的,都是數(shù)據(jù)。”[1]隨著數(shù)字和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進(jìn)步,在真實(shí)的物理空間外漸漸生成了一個(gè)全新的空間,即互聯(lián)網(wǎng)空間或者賽博空間。由于賽博空間對(duì)社會(huì)生活無所不在的影響力,它的鼓吹者們甚至以宣言的形式主張網(wǎng)絡(luò)主權(quán),號(hào)召“全世界的網(wǎng)民聯(lián)合起來”。[2]不同于傳統(tǒng)的管制領(lǐng)域,網(wǎng)絡(luò)世界具有虛擬性、開放性、共享性、傳播性等諸多新特點(diǎn),因此現(xiàn)有的政府監(jiān)管工具無法毫無阻礙地用之于日漸數(shù)據(jù)化的網(wǎng)絡(luò)世界,從而導(dǎo)致互聯(lián)網(wǎng)的治理成為問題,[3]而現(xiàn)有治理方式甚至超出了傳統(tǒng)法治的框架。[4]然而,互聯(lián)網(wǎng)空間治理反映的只是國(guó)家治理問題的一個(gè)側(cè)面,更深刻的危機(jī)在于,人、事件與活動(dòng)的數(shù)據(jù)化推動(dòng)國(guó)家自身的數(shù)據(jù)化,從而導(dǎo)致治理手段、方式和對(duì)象的內(nèi)在呈現(xiàn)一致化趨勢(shì)。世界的數(shù)據(jù)化讓國(guó)家治理處于雙重困境:其一,基于虛擬世界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二元區(qū)分而采用的傳統(tǒng)治理工具對(duì)數(shù)據(jù)治理失去控制力;其二,隨著數(shù)據(jù)化的進(jìn)程,作為手段的數(shù)據(jù)治理與治理對(duì)象的數(shù)據(jù)相混淆,使得治理活動(dòng)無從人手。治理理論依托國(guó)家理論,而國(guó)家理論與治理對(duì)象的捍格讓我們不得不反思治理活動(dòng)所賴以成立的前提,即傳統(tǒng)的主權(quán)國(guó)家理論。這一理論認(rèn)為,國(guó)家的核心要素是領(lǐng)土、主權(quán)和人口。然而,萬物互聯(lián)的數(shù)據(jù)洪流淹沒了主權(quán)國(guó)家的疆域,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國(guó)家概念疑竇叢生。換言之,可能并非數(shù)據(jù)、算法與人工智能出了問題而需要治理,而是國(guó)家概念不適應(yīng)時(shí)代的變遷。問題不是國(guó)家沒有足夠的手段治理數(shù)據(jù)世界,而是沒有將國(guó)家理解為數(shù)據(jù)國(guó)家。
? ? ? ?康德在認(rèn)識(shí)論上實(shí)現(xiàn)了“哥白尼式革命”,未經(jīng)批判的理性之所以在認(rèn)識(shí)上頻繁出現(xiàn)問題是因?yàn)樗偸羌僭O(shè)認(rèn)識(shí)主體要符合認(rèn)識(shí)對(duì)象。正如康德說,“我們不妨試一試,假定對(duì)象必須以我們的知識(shí)為轉(zhuǎn)移看看這樣一來我們?cè)谛味蠈W(xué)的任務(wù)中是不是有更好的進(jìn)展”。[5]康德調(diào)換了知識(shí)與對(duì)象的關(guān)系,從“知識(shí)必須符合對(duì)象”翻轉(zhuǎn)為“對(duì)象必須符合知識(shí)”,從而使知識(shí)的客觀性問題迎刃而解。與之相對(duì),在數(shù)據(jù)治理的問題上,或許不是數(shù)據(jù)治理本身存在問題,而是主體解決數(shù)據(jù)治理時(shí)所依賴的國(guó)家概念出了問題。反之,若形成了正確的國(guó)家概念,面對(duì)數(shù)據(jù)治理問題可能會(huì)有全新的視野和方法。在社會(huì)學(xué)意義上,現(xiàn)代國(guó)家被理解為領(lǐng)土、人口與主權(quán)。近代政治哲學(xué)將國(guó)家理解為所有自由人通過契約的政治聯(lián)合。馬克思主義者則認(rèn)為,國(guó)家是階級(jí)統(tǒng)治的工具。這些國(guó)家概念都可以回到基本秩序要素,國(guó)家無非是人的聯(lián)合以及人對(duì)人的統(tǒng)治。在數(shù)據(jù)時(shí)代,人以及對(duì)人的統(tǒng)治轉(zhuǎn)變?yōu)閿?shù)據(jù)以及對(duì)數(shù)據(jù)的處理,由此,在高度數(shù)據(jù)化以及算力極大擴(kuò)張的時(shí)代,基于技術(shù)對(duì)人類生存的干預(yù),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觀念有助于反思今天的數(shù)據(jù)治理。本文將以傳統(tǒng)國(guó)家的數(shù)據(jù)化為基礎(chǔ),思考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理念及其立法者,為數(shù)據(jù)治理提供一個(gè)框架性的國(guó)家觀念。為此,本文首先從歷史視角梳理技術(shù)與國(guó)家觀念的關(guān)系,提出數(shù)據(jù)國(guó)家乃是技術(shù)對(duì)國(guó)家進(jìn)行塑造的產(chǎn)物。其次,以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理念為前提,闡述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基本結(jié)構(gòu)及其特征。再次,立足于數(shù)據(jù)國(guó)家探討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立法者問題,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立法者不同于傳統(tǒng)的主權(quán)國(guó)家的主權(quán)者,它是算法、資本和人類政治空間的角逐,本文將以其為依據(jù)對(duì)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立法者進(jìn)行綜合分析。最后,本文認(rèn)為,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國(guó)家問題,其本質(zhì)是在一切被數(shù)據(jù)化的趨勢(shì)面前,如何捍衛(wèi)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自主性的問題。
? ? ? ?一、古典國(guó)家的淡出與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興起
? ? ? ?馬克思理論承認(rèn)生產(chǎn)力對(duì)社會(huì)秩序的改變是決定性的,從根本上來說,決定歷史進(jìn)程的還是技術(shù)。技術(shù)的創(chuàng)新導(dǎo)致秩序結(jié)構(gòu)的深刻變革。如果沒有技術(shù)參與社會(huì)秩序的塑造,很難想象,刀耕火種的民族會(huì)將自身組織成強(qiáng)大的利維坦。技術(shù)的可普遍化,首先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方式得以改進(jìn)。設(shè)若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物聯(lián)網(wǎng)以及各種通用的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全球化幾乎是不可能的。[6]若無全球化,民族國(guó)家危機(jī)就不再是需要認(rèn)真對(duì)待的問題。從西方歷史上觀察,對(duì)國(guó)家觀念形成重大影響的依然是技術(shù)。在技術(shù)的意義上,國(guó)家制度和形態(tài)就可以被理解為生產(chǎn)方式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西方歷史上古典社會(huì)和封建社會(huì)都可以從技術(shù)的角度來解釋,古典時(shí)代的奴隸制妨礙了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技術(shù)的發(fā)展從而限定了羅馬擴(kuò)張的極限,而封建制度的形成根源于農(nóng)業(yè)技術(shù)所限定的莊園經(jīng)濟(jì),由此導(dǎo)致主權(quán)的碎片化。[7]從古典國(guó)家向現(xiàn)代國(guó)家的轉(zhuǎn)型依然遵循了類似的技術(shù)邏輯,不僅技術(shù)理性參與了國(guó)家的建構(gòu),而且技術(shù)自身構(gòu)成了國(guó)家的結(jié)構(gòu)以及治理的手段。受到技術(shù)與理性的影響,國(guó)家呈現(xiàn)出兩種并存的趨勢(shì):世俗化和理性化。這一歷史過程被施米特把握為國(guó)家從神學(xué)階段走向倫理一人文階段到中立化時(shí)代的技術(shù)國(guó)家。[8]國(guó)家是一種人造的機(jī)器,現(xiàn)代法治國(guó)家已經(jīng)初步具備了某種數(shù)據(jù)化的特征,正如韋伯所分析的,“現(xiàn)代法官是自動(dòng)售貨機(jī),投進(jìn)去的是訴狀和訴訟費(fèi),吐出來的是判決和從法典上抄下的理由”。[9]然而隨著數(shù)據(jù)化與萬物互聯(lián)時(shí)代的到來,設(shè)想一種新的國(guó)家形態(tài)就是可能的。有人甚至可以設(shè)想當(dāng)今文明與以往文明的區(qū)別是本質(zhì)上的,在碳基文明時(shí)代(工業(yè)和農(nóng)業(yè)階段),權(quán)力和價(jià)值體現(xiàn)在空間上,暴力對(duì)短缺資源的極限控制;而在硅基文明時(shí)代(算力即權(quán)力),權(quán)力和價(jià)值體現(xiàn)在對(duì)算力資源的無限供給,從時(shí)間維度對(duì)概率的極限壓制。
? ? ? ?(一)主權(quán)國(guó)家與數(shù)據(jù)權(quán)力
? ? ? ?若以主權(quán)作為識(shí)別國(guó)家的標(biāo)志,那么依賴主權(quán)概念來認(rèn)識(shí)的國(guó)家可以統(tǒng)稱為古典國(guó)家。隨著信息和數(shù)據(jù)化的進(jìn)行,權(quán)力多元化和碎片化使得主權(quán)概念不足以分析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國(guó)家形態(tài),曾經(jīng)為君主或者人民掌握的權(quán)力逐漸流失。在數(shù)據(jù)時(shí)代,掌握權(quán)力變得越來越困難,正如美國(guó)《外交政策》的前編輯所言,國(guó)家對(duì)暴力的合法壟斷已陷入危機(jī),“在21世紀(jì),獲得權(quán)力更容易了,行使權(quán)力更難了,喪失權(quán)力更常見了”。[10]主權(quán)國(guó)家表達(dá)了權(quán)力集中性和獨(dú)立性的國(guó)家圖景,而進(jìn)入數(shù)據(jù)時(shí)代,主權(quán)概念被國(guó)家用來捍衛(wèi)自身的獨(dú)立性,以主權(quán)反對(duì)數(shù)據(jù)對(duì)主權(quán)的侵蝕,從而形成了奇特的主權(quán)觀念,即數(shù)據(jù)主權(quán)。[11]數(shù)據(jù)主權(quán)的提法分享了傳統(tǒng)主權(quán)國(guó)家的邏輯,其實(shí)質(zhì)依然是以主權(quán)概念來實(shí)現(xiàn)對(duì)數(shù)據(jù)的獨(dú)占。這種防守性的主權(quán)概念日益無法適應(yīng)大量數(shù)據(jù)的生產(chǎn)、控制與爭(zhēng)奪。一個(gè)弱國(guó)與一個(gè)數(shù)據(jù)公司相比,到底何者更享有主權(quán)已經(jīng)不再清晰可辨。
? ? ? ?自博丹提出主權(quán)概念以來,現(xiàn)代國(guó)家才呈現(xiàn)出“統(tǒng)治與服從”的秩序結(jié)構(gòu),在主權(quán)的概念下,一切政治沖突才得以被相對(duì)化,國(guó)家之內(nèi)取消了私斗,主權(quán)者保證國(guó)內(nèi)的和平、安寧和秩序。現(xiàn)代國(guó)家既是世俗的也是理性的,以人之尊嚴(yán)作為世俗時(shí)代的法權(quán)基礎(chǔ),將自身建構(gòu)為法治國(guó)家。科技的進(jìn)步加速了國(guó)家能力的建設(shè),工業(yè)進(jìn)步、資本主義、社會(huì)控制以及軍事力量的極大強(qiáng)化是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發(fā)展中的現(xiàn)代特征。[12]從蒸汽時(shí)代到電氣化時(shí)代,從電氣化時(shí)代進(jìn)入信息化時(shí)代,一方面現(xiàn)代國(guó)家不斷被科技所塑造,另一方面國(guó)家使用權(quán)力的手段開始多元化。從職能最小化的守夜人國(guó)家向介入社會(huì)領(lǐng)域的福利國(guó)家轉(zhuǎn)型,國(guó)家不僅要負(fù)責(zé)社會(huì)秩序和安全,還有承擔(dān)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職能,更進(jìn)一步,國(guó)家必須發(fā)展高科技以應(yīng)對(duì)國(guó)家間的競(jìng)爭(zhēng)。由此,國(guó)家對(duì)社會(huì)的干預(yù)廣泛而深入。國(guó)家并非借助于暴力對(duì)社會(huì)進(jìn)行治理而是利用統(tǒng)計(jì)學(xué)的宏觀手段對(duì)社會(huì)加以控制。權(quán)力顯示出對(duì)信息的高度依賴性,國(guó)家不斷發(fā)展和利用統(tǒng)計(jì)體系和統(tǒng)計(jì)技術(shù),而信息以及對(duì)信息的處理能力則是國(guó)家權(quán)力的重要來源。
? ? ? ?(二)數(shù)據(jù)主權(quán)與數(shù)據(jù)國(guó)家
? ? ? ?隨著信息與通信技術(shù)的發(fā)展,人、物以及組織被嵌入萬物互聯(lián)的網(wǎng)絡(luò)之中,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收集、存儲(chǔ)以及使用的組織和企業(yè)逐漸進(jìn)入傳統(tǒng)的被公共權(quán)力控制的領(lǐng)域,公權(quán)與私權(quán)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從而導(dǎo)致國(guó)家治理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為捍衛(wèi)國(guó)家在數(shù)據(jù)領(lǐng)域的優(yōu)勢(shì)地位,作為一個(gè)防守性的概念,數(shù)據(jù)主權(quán)的理論應(yīng)運(yùn)而生。與具有實(shí)體物理空間管轄領(lǐng)域的主權(quán)觀念不同,數(shù)據(jù)主權(quán)并無清晰的邊界,它指向的是大地、海洋和天空之外的虛擬空間。有論者認(rèn)為,數(shù)據(jù)主權(quán)是傳統(tǒng)主權(quán)在網(wǎng)絡(luò)世界的體現(xiàn),或者數(shù)據(jù)主權(quán)可以理解為國(guó)家對(duì)本國(guó)數(shù)據(jù)進(jìn)行管理和利用的權(quán)利,也有人將數(shù)據(jù)主權(quán)等同于一種能力,即對(duì)數(shù)據(jù)占有、處置和使用的能力。[13]撇開數(shù)據(jù)主權(quán)的具體定義,從主權(quán)的獨(dú)占性與最高性來看,它無非意味著傳統(tǒng)主權(quán)在信息時(shí)代的困境:第一,主權(quán)概念表現(xiàn)出國(guó)家對(duì)權(quán)力的壟斷,而數(shù)據(jù)主權(quán)則意味著國(guó)家不再是數(shù)據(jù)的唯一擁有者,個(gè)人、組織和其他國(guó)家都可以參與數(shù)據(jù)的爭(zhēng)奪和處置;第二,數(shù)據(jù)主權(quán)表達(dá)了公權(quán)與私權(quán)之邊界意識(shí)的模糊與消失,不同于屬人或?qū)俚氐臋?quán)力管轄,數(shù)據(jù)是流動(dòng)的,而數(shù)據(jù)空間是沒有界限的;第三,傳統(tǒng)主權(quán)所建立的秩序觀念不復(fù)存在,主權(quán)概念的內(nèi)涵是統(tǒng)治與服從關(guān)系,但是在數(shù)據(jù)領(lǐng)域和虛擬空間更多的是“無秩序的狀態(tài)”,各個(gè)組織都參與數(shù)據(jù)的爭(zhēng)奪。在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國(guó)家理論試圖在數(shù)據(jù)主權(quán)概念中尋求避風(fēng)港,恢復(fù)往日獨(dú)占和最高地位的榮光。然而,若以傳統(tǒng)主權(quán)觀念來理解國(guó)家,國(guó)家難以走出數(shù)據(jù)安全的艱難處境。隨著數(shù)據(jù)化進(jìn)程的加劇,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人工智能以及機(jī)器自我學(xué)習(xí)的技術(shù)嶄露鋒芒,以防守性姿態(tài)來應(yīng)對(duì)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挑戰(zhàn)越發(fā)顯得蒼白無力,因此有必要反思傳統(tǒng)的國(guó)家概念。當(dāng)窮盡主權(quán)國(guó)家所蘊(yùn)含的所有治理內(nèi)涵,尚不足以應(yīng)對(duì)數(shù)據(jù)上的無序和數(shù)據(jù)爭(zhēng)奪的不利地位的時(shí)候,從思維上我們就應(yīng)當(dāng)轉(zhuǎn)向?qū)?guó)家理論的反思。應(yīng)對(duì)數(shù)字時(shí)代的挑戰(zhàn),就需要一種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理念來回應(yīng)。與傳統(tǒng)國(guó)家理論將國(guó)家理解為領(lǐng)土、主權(quán)和人口的三要素不同,數(shù)據(jù)國(guó)家將國(guó)家理解為數(shù)據(jù)、算力與算法。領(lǐng)土有疆界,而數(shù)據(jù)無遠(yuǎn)弗屆,是自由流動(dòng)的信息之流;主權(quán)是對(duì)封閉空間的獨(dú)占與控制,而算力并非在封閉空間運(yùn)作,它是基于算力的比拼與協(xié)作;傳統(tǒng)主權(quán)國(guó)家的管理對(duì)象是個(gè)體與組織,而數(shù)據(jù)國(guó)家則需要對(duì)自動(dòng)化的決策程序即算法進(jìn)行整體協(xié)調(diào)。[14]
? ? ? ?(三)技術(shù)改變國(guó)家形態(tài)
? ? ? ?技術(shù)的進(jìn)步是數(shù)據(jù)國(guó)家理念形成的物質(zhì)基礎(chǔ),當(dāng)人、物和事件以數(shù)據(jù)的形式被網(wǎng)絡(luò)、傳感器和智能設(shè)備記錄、處理,并以高速運(yùn)動(dòng)的光電之流傳輸,可以說世界就被數(shù)據(jù)化了。數(shù)據(jù)國(guó)家理念的物質(zhì)基礎(chǔ)是數(shù)字技術(shù)。技術(shù)及相關(guān)的基礎(chǔ)設(shè)施是數(shù)據(jù)國(guó)家理念得以可能的物質(zhì)條件。在數(shù)據(jù)國(guó)家中,諸如政府、法律以及價(jià)值流通等領(lǐng)域都將以數(shù)字化形式表現(xiàn)出來。而且數(shù)據(jù)國(guó)家與傳統(tǒng)國(guó)家的巨大不同是,人與人關(guān)系模式的改變。在技術(shù)尚不成熟的時(shí)期,空間距離構(gòu)成了無法逾越的交往限制,然而在數(shù)據(jù)互聯(lián)的數(shù)據(jù)化時(shí)代,借助數(shù)字技術(shù),人挨人和人擠人的交往并非唯一的交往形式,甚至可以說并非必要的交往形式。這種技術(shù)數(shù)字交往的社會(huì)使得人際交往的無接觸成為可能。
? ? ? ?1.作為數(shù)據(jù)國(guó)家定在的基礎(chǔ)設(shè)施
? ? ? ?基礎(chǔ)設(shè)施是國(guó)家行動(dòng)的定在,[15]國(guó)家憑借強(qiáng)大的基礎(chǔ)設(shè)施獲得人、財(cái)、物快速流動(dòng)的能力。基礎(chǔ)設(shè)施構(gòu)筑了主體存在方式的物質(zhì)基礎(chǔ)。在主權(quán)國(guó)家時(shí)代,基礎(chǔ)設(shè)施體現(xiàn)為工業(yè)能力,它是經(jīng)濟(jì)概念。基礎(chǔ)設(shè)施是道路、橋梁、輸電線路以及油氣管道等。工業(yè)時(shí)代的基礎(chǔ)設(shè)施有其自身的特點(diǎn):第一,它具有附著性,即人的觀念和行動(dòng)只有附著于物質(zhì)基礎(chǔ)才是可能的;第二,它在物理上是有界限的,基礎(chǔ)設(shè)施受到領(lǐng)土邊界的限制,各國(guó)因其基礎(chǔ)設(shè)施水平的不同而體現(xiàn)出物流與工業(yè)能力的差異;第三,它具有人與對(duì)象之間不可通約性,人與物之間不會(huì)以基礎(chǔ)設(shè)施為中介相互化約為數(shù)據(jù)。進(jìn)入信息時(shí)代后,基礎(chǔ)設(shè)施的概念發(fā)生了實(shí)質(zhì)性的變化。基礎(chǔ)設(shè)施作為客體及其承載者可能化約為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承載著能量、價(jià)值甚至人的行動(dòng)。與工業(yè)文明的基礎(chǔ)設(shè)施相比較,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基礎(chǔ)設(shè)施則具有其無法比擬的特性,它超越了具體物理形態(tài)。數(shù)據(jù)基礎(chǔ)設(shè)施不再是中立性的技術(shù)手段,它實(shí)現(xiàn)了以價(jià)值承載者的形式來完成自我迭代與更新。而且數(shù)據(jù)基礎(chǔ)設(shè)施是實(shí)時(shí)性的,即產(chǎn)生即使用,以即時(shí)性取消了空間的限制。由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基礎(chǔ)設(shè)施的布置不再以特定中心為基礎(chǔ),而是多元、分布的去中心化結(jié)構(gòu)。以區(qū)塊鏈為例,每個(gè)數(shù)據(jù)節(jié)點(diǎn)都是數(shù)據(jù)存儲(chǔ)點(diǎn)和生產(chǎn)點(diǎn)。基礎(chǔ)設(shè)施的轉(zhuǎn)變意味著一種文明形態(tài)的生成。[16]而奠定數(shù)據(jù)時(shí)代之基礎(chǔ)設(shè)施的乃是5G、大數(shù)據(jù)、云計(jì)算、人工智能和物聯(lián)網(wǎng)等,這種技術(shù)變革被稱為人類社會(huì)的第四次工業(yè)革命。
? ? ? ?隨著5G設(shè)備的鋪設(shè),其低延時(shí)、廣連接和大寬帶的技術(shù)特性,滿足了客觀世界數(shù)據(jù)化進(jìn)程的要求。以此,人類開始迎接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帶來的文明形態(tài)的轉(zhuǎn)型,人類開始以技術(shù)植入來實(shí)現(xiàn)與數(shù)據(jù)的直接對(duì)接,數(shù)字化身份和認(rèn)證取代了生物特征的認(rèn)證,數(shù)字貨幣的流動(dòng)超越物理性限制,從而使得商業(yè)活動(dòng)無所不在,萬物互聯(lián)的前景成為可能。[17]展望未來,人類從未在文明意義上實(shí)現(xiàn)如此之高的一體化程度。
? ? ? ?2.作為算法的法律
? ? ? ?法律的產(chǎn)生來源于對(duì)秩序的需求,傳統(tǒng)法律的邏輯起點(diǎn)是個(gè)人。法律以個(gè)人為其邏輯起點(diǎn)來構(gòu)造秩序,并以理性的立法讓所有個(gè)人的欲望與意志得以共存。[18]然而,在數(shù)據(jù)時(shí)代,構(gòu)造秩序起點(diǎn)的個(gè)人逐漸向數(shù)據(jù)轉(zhuǎn)變,技術(shù)正在使人、物和事件得以被數(shù)據(jù)化,從而形成各式各樣的描寫、區(qū)分和評(píng)價(jià)。在秩序意義上,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真實(shí)自我”顯得越來越無關(guān)緊要。以此,立法者往往認(rèn)為現(xiàn)代法律體系面對(duì)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命題是如何以法律來規(guī)制數(shù)據(jù)。以此命題為前提,引發(fā)諸多關(guān)于個(gè)人信息保護(hù)、平臺(tái)規(guī)制以及數(shù)據(jù)使用權(quán)等法律問題。這些法律問題的產(chǎn)生,究其原因,在于以傳統(tǒng)主權(quán)國(guó)家理念來指導(dǎo)數(shù)據(jù)的治理。相反,若以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邏輯來思考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法律問題,那么,根據(jù)其權(quán)力形態(tài)的變化,就應(yīng)該以數(shù)據(jù)來理解法律。既然法律被理解為規(guī)則及其適用,那么對(duì)數(shù)據(jù)以及數(shù)據(jù)的收集、整理與運(yùn)算過程而言,法律就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認(rèn)知的計(jì)算及其處置。若將法律和算法都理解為實(shí)現(xiàn)特定目的而構(gòu)造出來的符號(hào)指令的集合,那么一旦實(shí)現(xiàn)對(duì)法律規(guī)則的符號(hào)化,就可以得出全新的法律形態(tài),這就是法律的算法化。[19]既然在數(shù)據(jù)時(shí)代,誰掌握數(shù)據(jù)挖掘和整理的能力誰就在輸出社會(huì)規(guī)范,由此,立法者也就不一定限于壟斷傳統(tǒng)公權(quán)力的國(guó)家。
? ? ? ?3.作為財(cái)產(chǎn)的數(shù)據(jù)
? ? ? ?生活世界數(shù)據(jù)化的另一個(gè)顯著的結(jié)果就是財(cái)富形態(tài)的改變。財(cái)富形態(tài)從具有物質(zhì)特征的貴重金屬、自然資源開始向知識(shí)、數(shù)據(jù)和信息形態(tài)轉(zhuǎn)變。數(shù)據(jù)成為繼土地、資本和勞動(dòng)力之后的財(cái)產(chǎn)形態(tài),也有人將其稱為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石油”。[20]雖然在人類歷史上信息一旦被公開就進(jìn)入了人人皆可以取用的公共領(lǐng)域,從而不再具有財(cái)產(chǎn)的排他性特征,但是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數(shù)據(jù)財(cái)產(chǎn)形式不受此限制。如德姆塞茨認(rèn)為,“當(dāng)內(nèi)部化收益大于成本時(shí),產(chǎn)權(quán)就會(huì)產(chǎn)生”,而數(shù)據(jù)之所以被認(rèn)為是一種財(cái)產(chǎn),可以從產(chǎn)權(quán)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角度予以理解。因?yàn)閾碛袛?shù)據(jù)并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析,從而為決策提供依據(jù)。擁有數(shù)據(jù)和數(shù)據(jù)的分析能力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從而可以被產(chǎn)權(quán)化。從法學(xué)上觀察,在財(cái)產(chǎn)上數(shù)據(jù)顯示出與一般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相似的權(quán)利特征,即財(cái)產(chǎn)客體的經(jīng)濟(jì)性、可特定性和可轉(zhuǎn)讓性。[21]由于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出現(xiàn)以及數(shù)據(jù)生產(chǎn)和挖掘的算力技術(shù)的提升,尤其是大數(shù)據(jù)的出現(xiàn),數(shù)據(jù)將成為一種重要的資源。人類通過移動(dòng)終端而被接入互聯(lián)網(wǎng),海量的信息被生產(chǎn)和收集,通過強(qiáng)大算力的數(shù)據(jù)加工,具有價(jià)值的數(shù)據(jù)被生產(chǎn)出來。[22]大數(shù)據(jù)技術(shù)讓零散的、海量的、看似無關(guān)聯(lián)的數(shù)據(jù)整合為有價(jià)值的信息。而從實(shí)踐上看,數(shù)據(jù)財(cái)產(chǎn)的確權(quán)以及交易規(guī)則也逐漸被承認(rèn)。[23]數(shù)據(jù)財(cái)產(chǎn)權(quán)作為數(shù)字秩序的重要構(gòu)成部分,構(gòu)成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價(jià)值流通的基礎(chǔ),而這種數(shù)據(jù)集中性的財(cái)產(chǎn)形式就是數(shù)字貨幣。與以銀行記賬為基礎(chǔ)的支付工具的電子貨幣不同的是,數(shù)字貨幣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存在,從而做到價(jià)值的代碼化。數(shù)字貨幣將成為匿名的、可編輯的和算法性的賬本技術(shù)。由此,在數(shù)據(jù)時(shí)代,數(shù)字貨幣突破了傳統(tǒng)以主權(quán)國(guó)家為擔(dān)保的貨幣信用制度,僅憑虛擬的數(shù)字、去中心化的記賬機(jī)制而自動(dòng)發(fā)行,從而逃避主權(quán)國(guó)家的追蹤。法定貨幣作為主權(quán)國(guó)家的重要標(biāo)志在數(shù)字時(shí)代被虛擬的一串?dāng)?shù)字所突破。
? ? ? ?4.無接觸的社會(huì)
? ? ? ?技術(shù)的進(jìn)步使社會(huì)交往模式發(fā)生變化,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到來使得無接觸的社會(huì)到來成為可能。社會(huì)構(gòu)成需要人際之前的交往,受制于技術(shù)限制,人際交往通常需要相互接觸,無接觸的社會(huì)既無法建構(gòu)人際信任,也無法傳達(dá)生活世界的共同態(tài)度、共識(shí)和團(tuán)結(jié)精神。傳統(tǒng)社會(huì)建構(gòu)身份認(rèn)同的方式就是通過接觸來實(shí)現(xiàn)情感、認(rèn)知和態(tài)度上的連接。群際社會(huì)接觸理論認(rèn)為頻繁的社會(huì)接觸有助于人們之間的信息交換、相互了解、增強(qiáng)信任從而消除沖突。因此,對(duì)于消除偏見和建構(gòu)社會(huì)聯(lián)系來說,即使是在物理上無接觸的群體,也要想象性地接觸來建構(gòu)情感聯(lián)系。由于技術(shù)的進(jìn)步使人際交往的范圍極大擴(kuò)張,從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huì)向陌生人的社會(huì)轉(zhuǎn)變,當(dāng)人際交往借助數(shù)據(jù)媒體而得以完成時(shí),面對(duì)面的模式轉(zhuǎn)變?yōu)闊o接觸的數(shù)碼媒體模式,社會(huì)信任并不一定以面對(duì)面的交往為前提。[24]人際交往呈現(xiàn)不接觸的虛擬特征,在AR技術(shù)的支持下,人們得以通過數(shù)據(jù)媒介分享觀點(diǎn)、傳達(dá)感受,虛擬和現(xiàn)實(shí)之間的界限開始模糊,而生存之所需可以通過不接觸而直接以網(wǎng)絡(luò)的方式提供。絕大多數(shù)需要人挨人、人碰人才得以完成的社會(huì)活動(dòng),借助及時(shí)高效的數(shù)據(jù)網(wǎng)絡(luò)就可以完成。
? ? ? ?二、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特征
? ? ? ?國(guó)家作為一種秩序形態(tài),它受制于人類的認(rèn)識(shí)能力。在人類歷史早期,人們憑借感性直觀和想象來理解秩序,國(guó)家乃是人神共居的秩序形態(tài)。在秩序被理性化之前,人神關(guān)系構(gòu)成人類理解秩序的基本框架,從瞬間神到專職神最后以基督教上帝為代表的單一神,它們都是人類構(gòu)造秩序的精神支點(diǎn)。[25]哲學(xué)興起后,人成為哲學(xué)的第一原理,柏拉圖創(chuàng)建了理念王國(guó),中世紀(jì)的上帝代替理性,世俗國(guó)家依舊處在上帝的神圣秩序之下。在馬基雅維利之后,國(guó)家獲得獨(dú)立性,歷史取代理性成為第一原則。[26]黑格爾將歷史與理性結(jié)合起來,國(guó)家不僅是絕對(duì)精神的承擔(dān)者,更是歷史的最終形式。現(xiàn)代國(guó)家理論總是圍繞著權(quán)力的組織形式也就是政體狀態(tài)展開。到馬克斯·韋伯為止,國(guó)家獲得其現(xiàn)代形態(tài),即理性國(guó)家。理性國(guó)家是現(xiàn)代國(guó)家的理想類型,啟蒙時(shí)代以來人們希望以理性的方式來壟斷暴力,并支配其疆域內(nèi)的居民。國(guó)家可以理解為被壟斷的暴力、被暴力支配的個(gè)人以及特定疆域的秩序之狀態(tài)。現(xiàn)代國(guó)家總體上呈現(xiàn)出一種理性構(gòu)筑的金字塔結(jié)構(gòu),頂端是被國(guó)家壟斷的暴力,作為法理型支配類型,合法性是其支配的正當(dāng)性來源,國(guó)家行使暴力的方式是形式化的法律,借助于官僚制層級(jí)性運(yùn)作,國(guó)家權(quán)力得以運(yùn)用于個(gè)體與社會(huì)諸領(lǐng)域。在這種國(guó)家圖景當(dāng)中,“政治”就被理解為社會(huì)團(tuán)體分享權(quán)力或影響權(quán)力的努力。[27]但是,一旦進(jìn)入數(shù)據(jù)時(shí)代,在人、物和事件被數(shù)據(jù)化的世界中,人類理性的能力不足以處理海量的數(shù)據(jù),由此就發(fā)生了圍繞國(guó)家三要素的變革,受到秩序支配的不再是公民個(gè)體而是數(shù)據(jù),而處理數(shù)據(jù)的不是理性而是算法,算法的能力依賴于強(qiáng)大的算力,誰掌握算力誰就擁有了主導(dǎo)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權(quán)力。在數(shù)據(jù)的世界中,空間概念不再依附于物理性的疆域,它展現(xiàn)出一幅數(shù)據(jù)海洋的形態(tài),而傳統(tǒng)國(guó)家就好像漂浮于數(shù)據(jù)海洋中的小舟。
? ? ? ?(一)人的數(shù)據(jù)化與人工智能
? ? ? ?在古典時(shí)代,人被分解為靈魂與身體的二元結(jié)構(gòu),靈魂與身體的二分被設(shè)想為秩序的起點(diǎn),以受理性支配的靈魂來約束受感性支配的身體,在內(nèi)心中的約束力是道德,而外在的強(qiáng)制規(guī)則是法律。[28]自由的理性存在者是國(guó)家秩序得以成立的邏輯起點(diǎn),而讓理性存在者符合規(guī)則也是秩序得以可能的終點(diǎn)。但是,在數(shù)據(jù)時(shí)代,在人、物和實(shí)踐都被數(shù)據(jù)化之后,人作為不可分的對(duì)象[29]并非無可置疑,隨著技術(shù)的進(jìn)步,秩序的最小單元是否為人已經(jīng)疑竇叢生。事到如今,人的身體可以通過技術(shù)而直接接人數(shù)據(jù)系統(tǒng),支配人類行為的法律和道德模式從而不再構(gòu)成秩序生成的唯一方式。古典秩序的起點(diǎn)是靈魂與身體不可分割的個(gè)體,而現(xiàn)代秩序的起點(diǎn)則是諸多以數(shù)據(jù)化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的對(duì)象。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統(tǒng)治對(duì)象不再是作為個(gè)體的人,而是數(shù)據(jù)。導(dǎo)致這一結(jié)果的是兩個(gè)同時(shí)發(fā)生的過程,即人的數(shù)據(jù)化與數(shù)據(jù)的人化。伴隨著這兩種趨勢(shì)同時(shí)發(fā)生的是萬物的互聯(lián),這導(dǎo)致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統(tǒng)治對(duì)象的網(wǎng)絡(luò)化,人類秩序的結(jié)構(gòu)不再是金字塔式的層級(jí)結(jié)構(gòu),而是由算力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的網(wǎng)狀結(jié)構(gòu)。
? ? ? ?第一是人的數(shù)據(jù)化。人的數(shù)據(jù)化既是一種技術(shù)導(dǎo)致的必然發(fā)生的歷史過程,也是人自身地位逐漸喪失的倫理處境。人的數(shù)據(jù)化包括由淺入深的三個(gè)層次:人的身份的數(shù)據(jù)化、人機(jī)融合以及意識(shí)的數(shù)據(jù)化。人的身份的數(shù)據(jù)化是人的“自然人”形象的轉(zhuǎn)變,人類活動(dòng)痕跡的數(shù)據(jù)化可以讓人在數(shù)據(jù)世界中擁有自身的數(shù)據(jù)身份,這也構(gòu)成識(shí)別和支配人的數(shù)據(jù)基礎(chǔ)。接著是人機(jī)融合,新技術(shù)革命使得機(jī)器與人腦的連接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變?yōu)楝F(xiàn)實(shí)。瑞典的某科技公司以半無痛的方式,在一分鐘之內(nèi)向其員工植入如米粒般大小的芯片。雖然在人體內(nèi)植入芯片在倫理上引發(fā)了諸多爭(zhēng)議,[30]但是在人體中植入芯片從技術(shù)上已經(jīng)開始應(yīng)用于醫(yī)學(xué)、金融以及軍事等領(lǐng)域。除此之外,借助于芯片技術(shù),人可以直接接人數(shù)據(jù)以達(dá)成人機(jī)互聯(lián)的效果。而更令人恐懼的是人的意識(shí)的數(shù)據(jù)化過程。以身心二元論的哲學(xué)前提來建構(gòu)秩序的邏輯面臨失效的風(fēng)險(xiǎn),若人類意識(shí)可以無須經(jīng)由語言作為交流的中介,而是借由數(shù)據(jù)的通信網(wǎng)絡(luò)來實(shí)現(xiàn)傳輸,那么毫無疑問,這不僅將使秩序的模式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甚至以語言為基礎(chǔ)的文化概念也可能遭到顛覆性的變革。
? ? ? ?第二是數(shù)據(jù)的人化。與人逐漸被數(shù)據(jù)化的過程相伴,算法、數(shù)據(jù)以及高傳輸性能的提升導(dǎo)致的另一個(gè)趨勢(shì)就是數(shù)據(jù)的人化,這就是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人工智能。以Alpha Go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已經(jīng)展示出在人類擅長(zhǎng)的領(lǐng)域中的卓越性,隨著展望人工智能在定位、導(dǎo)航、家居服務(wù),以及模仿人類心智等領(lǐng)域所帶來的便利性,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威脅值得警惕。人工智能已經(jīng)從一個(gè)知識(shí)論問題轉(zhuǎn)變?yōu)橐粋€(gè)存在問題,[31]當(dāng)人工智能突破奇點(diǎn)而獲得自由意志和情感能力,人就并非參與政治秩序塑造的唯一主體。一旦人工智能在存在論層面參與秩序的構(gòu)造過程,將大幅度修改影響公平、公正、權(quán)利等習(xí)以為常的社會(huì)游戲規(guī)則。
? ? ? ?第三是萬物互聯(lián)。萬物互聯(lián)的本質(zhì)性變革在于從物與物的互聯(lián)轉(zhuǎn)變?yōu)槿伺c物的互聯(lián),物具有更強(qiáng)的敏感性而非毫無生命的客觀對(duì)象,當(dāng)物與人相連接就產(chǎn)生萬物數(shù)據(jù)化的后果。“物”與“物”可以通過高速傳輸?shù)臄?shù)據(jù)而彼此“感知”對(duì)方的存在,主體客體的關(guān)系不再清晰可辨,人類社會(huì)正在邁向萬物互聯(lián)(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時(shí)代。[32]純粹的自然性在消失,主體和客體相互嵌入,一切化約為數(shù)據(jù)流、代碼以及分布式網(wǎng)絡(luò),而海量數(shù)據(jù)依賴分布式的云計(jì)算來處理,基于理性與自由的平等交易模式將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從國(guó)家權(quán)力支配的對(duì)象上看,人類社會(huì)的組織形態(tài)也將依賴于日漸重要的人工智能與復(fù)雜算法,面對(duì)海量的數(shù)據(jù)資源,國(guó)家秩序和安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 ? ? ?(二)從權(quán)力到算力
? ? ? ?在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公權(quán)力的地位不斷受到侵蝕,具備自主學(xué)習(xí)和決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因在數(shù)據(jù)占有和技術(shù)上的優(yōu)勢(shì),逐漸形成一種算法權(quán)力。算法權(quán)力的出現(xiàn)不僅與理性國(guó)家的公權(quán)力形成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而且由于算法權(quán)力無需任何正當(dāng)性資源,尤其是其過度的資本化和不透明性使得現(xiàn)代國(guó)家的公共權(quán)力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jī)。
? ? ? ?權(quán)力,就其本質(zhì)來說無非是實(shí)現(xiàn)目的之手段。韋伯認(rèn)為,“權(quán)力意指行動(dòng)者在一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中,可以貫徹其意志的機(jī)會(huì),而不論這種機(jī)會(huì)的社會(huì)基礎(chǔ)是什么”。[33]當(dāng)這種權(quán)力用于捍衛(wèi)公共利益之時(shí),這樣的權(quán)力才可以被稱為公權(quán)力。公權(quán)力的來源、構(gòu)成及其運(yùn)用是現(xiàn)代國(guó)家的核心議題。一般來說,被國(guó)家獨(dú)占的公權(quán)力,在來源上要具備正當(dāng)性,在使用目的上應(yīng)該指向公共利益,而為了使公權(quán)力不至于濫用,現(xiàn)代政治采取一種將公權(quán)力之所有權(quán)與行使權(quán)予以區(qū)分的做法,并且還對(duì)行使權(quán)力的主體施加相當(dāng)嚴(yán)格的法律程序條件和政治責(zé)任。而算法權(quán)力最早作為一種依附于資本的科技力量逐漸具備了“準(zhǔn)公權(quán)力”的特征,它直接介入社會(huì)治理的各個(gè)領(lǐng)域,它不以直接的暴力來實(shí)現(xiàn)自身的目的,它對(duì)數(shù)據(jù)網(wǎng)絡(luò)的控制是通過接口控制、數(shù)據(jù)信號(hào)、程序演算等隱蔽手段來實(shí)現(xiàn)對(duì)公共議程的支配。算法權(quán)力是沒有正當(dāng)性來源的匿名權(quán)力,權(quán)力的運(yùn)作不服從人為設(shè)定的規(guī)范,它不遵守規(guī)范和程序,甚至自身就可以生產(chǎn)規(guī)范。算法權(quán)力對(duì)公權(quán)力的侵蝕和異化,既無跡可尋,又自由無礙。作為一種戴著自由貿(mào)易的商業(yè)面具的權(quán)力,其商業(yè)邏輯先于治理,利益偏好無視平等原則,奉行技術(shù)理性高于價(jià)值理性,在秩序生成上隱性運(yùn)行取代公權(quán)力的赤裸暴力。[34]
? ? ? ?人類建構(gòu)國(guó)家與公共權(quán)力是為了在不確定性的海洋中構(gòu)筑確定性的島嶼,人們?cè)V諸法律的客觀性以尋求秩序的穩(wěn)定性。然而,在數(shù)據(jù)時(shí)代,當(dāng)算法權(quán)力介入人類的法律事務(wù),由于其自身的黑箱化和“透明社會(huì)”,算法是否會(huì)發(fā)展成為一種更為獨(dú)裁專斷的力量,使人類追求客觀性和確定性的努力滑向絕對(duì)主觀性的算法獨(dú)裁,這一點(diǎn)尤其值得警惕。[35]
? ? ? ?(三)從律法到算法
? ? ? ?以法律規(guī)范來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治理是現(xiàn)代國(guó)家理性成熟的標(biāo)志,然而以人定法制定規(guī)范以約束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算法并予以規(guī)制,則日益顯得捉襟見肘。面對(duì)海量的數(shù)據(jù),法律既不可能對(duì)算法的內(nèi)容進(jìn)行道德審查,也無法根據(jù)權(quán)利原則確定其內(nèi)容是否屬于言論自由的范疇,亦不可能就其制定標(biāo)準(zhǔn)和算力進(jìn)行技術(shù)限制。因?yàn)榧夹g(shù)上的門檻和壁壘極有可能使公權(quán)力的監(jiān)控努力付諸流水。[36]面對(duì)算法自主性的生成,出現(xiàn)了兩種思路來處理算法與法律規(guī)范的關(guān)系:一是將法律與算法視為兩種本質(zhì)上不同的事物,并以法律對(duì)算法施加規(guī)制,這種看法可以稱為法律與算法的二元論;二是從規(guī)制的本質(zhì)出發(fā),認(rèn)為法律與算法都是規(guī)則,這種觀點(diǎn)可以稱為法律與算法的一元論。
? ? ? ?算法與法律二元論的目的是以法律來規(guī)制算法,從而達(dá)到法律捍衛(wèi)政治社會(huì)客觀價(jià)值的目的。這一思路認(rèn)為,算法的運(yùn)用將導(dǎo)致人的主體性喪失、公權(quán)力被侵蝕以及社會(huì)偏離公正等惡果,一言以蔽之,算法將帶來社會(huì)秩序的危機(jī)。為此,二元論者呼吁從法律的角度對(duì)算法進(jìn)行治理。[37]在法律實(shí)踐上,如歐盟通過強(qiáng)化個(gè)體權(quán)利來對(duì)自動(dòng)化決策程序進(jìn)行約束,具體做法上賦予個(gè)體以新型的數(shù)據(jù)權(quán)利來控制自動(dòng)化決策的干預(yù)能力。而在美國(guó),立法者通過立法來對(duì)算法進(jìn)行問責(zé),從而實(shí)現(xiàn)對(duì)平臺(tái)與算法的監(jiān)管。與歐美不同,我國(guó)對(duì)算法治理的模式是將治理對(duì)象設(shè)定為平臺(tái),以設(shè)定算法義務(wù)和權(quán)利的方式來落實(shí)對(duì)算法的多元化治理。[38]二元論得以成立的前提是算法本身的可治理性,窮盡法律技術(shù)的可能性來規(guī)制算法。不過,應(yīng)該考慮到的是,當(dāng)算法的自主性在技術(shù)和數(shù)據(jù)量級(jí)上超越了法律的技術(shù)水平和知識(shí)能力,則法律不僅無法規(guī)制算法,反倒有可能遭遇到算法的反制。由此,有觀察者指出,“人工智能技術(shù)可能不只是理工科專業(yè)人士的領(lǐng)域,法律人士以及其他治理者也需要學(xué)習(xí)人工智能知識(shí),這對(duì)法律人士和其他治理者提出了技術(shù)要求”。[39]
? ? ? ?算法與法律一元論的觀點(diǎn)打破了法律規(guī)范和算法之間的區(qū)別,它承認(rèn)了算法具有規(guī)范的生產(chǎn)能力。在最表面的意義上,算法與法律都是為實(shí)現(xiàn)特定目標(biāo)構(gòu)造的指令集,二者都可以成為社會(huì)治理的技術(shù)手段。[40]更進(jìn)一步,當(dāng)法律以符號(hào)化的方式予以制定和運(yùn)作時(shí),那么法律與算法之間不再?zèng)芪挤置鳎叩膮^(qū)別逐漸消融。既然認(rèn)知可以通過符號(hào)化的方式進(jìn)行計(jì)算,那么作為人類意識(shí)成果的立法、執(zhí)行和司法就不是不可取代的。這一過程正在被技術(shù)進(jìn)步所強(qiáng)化,不僅法律知識(shí)作為被編碼的符號(hào)可以被存貯和運(yùn)算,甚至算法可以在事實(shí)與規(guī)范之間流轉(zhuǎn),而且可以轉(zhuǎn)化為確定性的法律效果。[41]算法作為規(guī)范的生產(chǎn)者,不僅不是一個(gè)想象的產(chǎn)物,而且正在成為一個(gè)現(xiàn)實(shí)性的后果。從平臺(tái)的人工智能操作對(duì)用戶進(jìn)行打分的實(shí)踐來看,算法權(quán)力正以規(guī)范的形式來對(duì)用戶施加控制力。[42]從其整個(gè)制定標(biāo)準(zhǔn)、打分和懲罰的過程來看,幾乎與一個(gè)司法過程相當(dāng)。
? ? ? ?(四)從領(lǐng)土到數(shù)據(jù)
? ? ? ?在確定的疆域內(nèi)壟斷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這是現(xiàn)代主權(quán)國(guó)家的基本特征。而所謂疆域,即英文的territory,來自拉丁文的territorium,而terra就是土地,“Terra意味著土地、大地、營(yíng)養(yǎng)、給養(yǎng),讓人感受到是一種歷久彌堅(jiān)的介質(zhì)”,而其最早的含義是“恐嚇、嚇唬”,由此territorium意旨“人們受到警告的地方”。[43]領(lǐng)土最初的形式是以政治權(quán)力控制城鎮(zhèn)周邊的領(lǐng)地,隨著航海技術(shù)的進(jìn)步,國(guó)家的邊界從陸地伸向海洋,而當(dāng)人類以航空器翱翔天際的時(shí)候,國(guó)家的疆域從陸地到海洋再到伸向天空。國(guó)家權(quán)力必然要在確定性的空間享有最高的支配權(quán),隨著信息與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到來,讓所有的物理空間不再適用,尤其是當(dāng)虛擬空間與真實(shí)空間界限不分的時(shí)候,國(guó)家如何再次集中權(quán)力以構(gòu)造秩序就顯得疑問重重。值得反思的是,技術(shù)是導(dǎo)致國(guó)家疆域變更的根本原因,技術(shù)不僅塑造疆域的類型(領(lǐng)土、領(lǐng)海和領(lǐng)空,以及數(shù)據(jù)世界),還決定了國(guó)家主權(quán)的輻射范圍。[44]
? ? ? ?網(wǎng)絡(luò)空間的形成對(duì)傳統(tǒng)國(guó)家主權(quán)觀念下的領(lǐng)土觀念構(gòu)成挑戰(zhàn),與領(lǐng)土、領(lǐng)海和領(lǐng)空不同的是,網(wǎng)絡(luò)空間的構(gòu)成既有實(shí)體性的基礎(chǔ)設(shè)施又有虛擬性的數(shù)據(jù)流動(dòng)。構(gòu)成互聯(lián)網(wǎng)結(jié)構(gòu)的是作為底層的物理層,中間的邏輯層以及作為頂層的內(nèi)容層。[45]國(guó)家權(quán)力對(duì)互聯(lián)網(wǎng)領(lǐng)域的控制也就表現(xiàn)為根據(jù)三個(gè)不同層次進(jìn)行分類干預(yù)以及立法。[46]由于互聯(lián)網(wǎng)關(guān)系到國(guó)家整體的安全和秩序,由此誕生了數(shù)據(jù)主權(quán)的概念。這一概念試圖將領(lǐng)土主權(quán)時(shí)代的主權(quán)觀念無差別地運(yùn)用于互聯(lián)網(wǎng)空間。它預(yù)設(shè)了互聯(lián)網(wǎng)空間作為虛擬空間是國(guó)家領(lǐng)土在互聯(lián)網(wǎng)世界的延伸。然而,真正讓國(guó)家主權(quán)觀念遭受到巨大挑戰(zhàn)的不是虛擬空間與真實(shí)空間的二元區(qū)分,而是所謂虛擬的空間已與現(xiàn)實(shí)空間無法區(qū)分。換言之,國(guó)家面對(duì)的治理空間,不再是真實(shí)可見的物理存在,而是數(shù)據(jù)之流。
? ? ? ?這就導(dǎo)致了另一個(gè)概念的產(chǎn)生,即數(shù)據(jù)主權(quán)。數(shù)據(jù)主權(quán)認(rèn)為,網(wǎng)絡(luò)空間只是國(guó)家領(lǐng)土向虛擬世界的延伸。然而,在數(shù)據(jù)時(shí)代,當(dāng)人、物以及事件被數(shù)據(jù)化之后,不僅國(guó)家權(quán)力被數(shù)據(jù)化了,其權(quán)力運(yùn)作對(duì)象同樣也被數(shù)據(jù)化了。在歷史上,領(lǐng)土概念構(gòu)成了國(guó)家存在的物質(zhì)基礎(chǔ)以及國(guó)家權(quán)力行使的封閉空間,是“法律秩序的屬地效力范圍”。[47]按照領(lǐng)土對(duì)國(guó)家的構(gòu)成性特征,領(lǐng)土具有完整性、排他性以及人民自決原則。[48]與領(lǐng)土概念相比,數(shù)據(jù)空間具有全然不同的特性。首先,數(shù)據(jù)空間是非物理性的,即沒有可供辨識(shí)的實(shí)體。其次,領(lǐng)土的完整性要求權(quán)力上的統(tǒng)一性和不可分割,而數(shù)據(jù)空間各國(guó)共享基礎(chǔ)設(shè)施并且借由網(wǎng)絡(luò)而相互聯(lián)結(jié)和滲透,它既是可以分割的又是相互依賴的。為此,各國(guó)試圖以局域網(wǎng)的方式來保持自身的獨(dú)立性,然而在一般條件下,局域網(wǎng)的斷開是不可設(shè)想的。[49]再次,領(lǐng)土的排他性決定了同一片土地上不可能出現(xiàn)相互競(jìng)爭(zhēng)的權(quán)力,它必然專屬于一個(gè)權(quán)力主體。然而在數(shù)據(jù)空間當(dāng)中,對(duì)數(shù)據(jù)的獨(dú)占和享有不僅在技術(shù)上可能逃避了國(guó)家的管控,而且在算力水平上,商業(yè)機(jī)構(gòu)和云計(jì)算等因其技術(shù)上的唯一性,使得數(shù)據(jù)空間中的諸多領(lǐng)域成為國(guó)家權(quán)力無法觸及的空間。最后,領(lǐng)土由民族之自決以決定其歸屬,而在數(shù)據(jù)空間當(dāng)中,既無法識(shí)別哪些是被團(tuán)結(jié)起來的政治意志,也無法在民主原則上解決數(shù)據(jù)歸屬問題,甚至數(shù)據(jù)歸屬本身也不具有確定的邊界。數(shù)據(jù)無法確定其邊界,它是流動(dòng)性的存在。
? ? ? ?三、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立法者
? ? ? ?網(wǎng)絡(luò)空間是物理空間在互聯(lián)網(wǎng)世界的延伸,由此產(chǎn)生的問題是,傳統(tǒng)的民族國(guó)家在網(wǎng)絡(luò)空間中如何尋找自身的角色和定位。這樣的命題可以表述為:如何以舊國(guó)家來治理新世界。而回到理性國(guó)家的誕生之初,古典的主權(quán)國(guó)家無非是人為建構(gòu)的秩序共同體。正如霍布斯將國(guó)家比喻為復(fù)雜的機(jī)器,它是“人造的有朽的上帝”。[50]制造國(guó)家之材料也是人,而其制作方式是在理性中賦予契約的因素。與現(xiàn)代國(guó)家的構(gòu)造方式不同的是,網(wǎng)絡(luò)空間亦是人造之物,制造它的材料是數(shù)據(jù),而制造的方式是算法與編碼。由此可以推論,網(wǎng)絡(luò)空間并非主權(quán)者治理之對(duì)象,而是網(wǎng)絡(luò)構(gòu)成數(shù)據(jù)國(guó)家之外表。作為有自主性生成邏輯與運(yùn)行規(guī)律的數(shù)據(jù)國(guó)家,它在權(quán)力主體、運(yùn)作方式和對(duì)象上與傳統(tǒng)主權(quán)國(guó)家存在諸多不同。僅從數(shù)據(jù)的外觀尚不足以使得數(shù)據(jù)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狀態(tài)獲得國(guó)家的政治性和整體性,而必然觸及國(guó)家的一個(gè)關(guān)鍵性概念:數(shù)據(jù)國(guó)家中誰說了算。數(shù)據(jù)國(guó)家依賴新科技革命的技術(shù)成就,在數(shù)據(jù)世界中,國(guó)家的統(tǒng)一性、完整性以及至上性的消失,也就造成了對(duì)權(quán)力壟斷的唯一性的喪失。由此,圍繞技術(shù)本身產(chǎn)生三種立法者:一是控制技術(shù)的立法者——資本;二是技術(shù)自主性的立法者——人工智能;三是抵制技術(shù)捍衛(wèi)人類主體性的立法者——政治國(guó)家。
? ? ? ?(一)資本作為立法者
? ? ? ?一般來說,技術(shù)作為達(dá)成人類目的的手段,是中性的,無所謂善惡。然而,隨著技術(shù)對(duì)人類生活方式的深刻改造,這種技術(shù)中立論已經(jīng)在倫理檢討面前無法自證清白。事實(shí)上,技術(shù)是人類設(shè)計(jì)和構(gòu)造的,創(chuàng)造之初并非沒有特定的目的。而驅(qū)動(dòng)技術(shù)進(jìn)步的最直接因素,無疑是資本的逐利性。馬克思以驚人的見識(shí)很早就意識(shí)到技術(shù)的革命性影響,第一次工業(yè)革命后,馬克思犀利地指出,“蒸汽、電力和自動(dòng)紡機(jī)甚至是比巴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xiǎn)萬分的革命家”。[51]以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jù)、云計(jì)算等技術(shù)為主導(dǎo)的第四次工業(yè)革命不僅深刻地改變了社會(huì)運(yùn)行的方式,而且讓資本開始深入社會(huì)的幾乎每一個(gè)領(lǐng)域。具有資本優(yōu)勢(shì)的大型技術(shù)公司不僅利用資本占據(jù)了技術(shù)的制高點(diǎn),而且深度介入了公權(quán)力的運(yùn)行過程。
? ? ? ?諸如蘋果、谷歌、阿里巴巴、騰訊等大型科技公司,這些以資本集聚為特征的超級(jí)行為體,由于掌握了大量的數(shù)據(jù)以及強(qiáng)大的計(jì)算能力,它們完全有能力局部修改社會(huì)生活規(guī)則,由此衍生出“新的政治空間”,不僅壓縮了傳統(tǒng)公權(quán)力的覆蓋范圍和監(jiān)管能力,而且還在持續(xù)地重塑“國(guó)家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52]資本與數(shù)據(jù)的結(jié)合構(gòu)成全新的權(quán)力運(yùn)作形態(tài),它以數(shù)據(jù)資本主義的形式為數(shù)據(jù)國(guó)家立法。這一過程的發(fā)生機(jī)制是,資本通過對(duì)技術(shù)投入而掌握算法,算法作為一種權(quán)力形態(tài)向秩序領(lǐng)域滲透,而操縱算法權(quán)力的正是民族國(guó)家難以識(shí)別的匿名資本。資本權(quán)力穿透民族國(guó)家的邊界,由于其掌握海量的數(shù)據(jù)以及強(qiáng)大的算力,在這場(chǎng)與民族國(guó)的競(jìng)爭(zhēng)中逐漸顯現(xiàn)出優(yōu)勢(shì)。如果資本壟斷數(shù)據(jù)以及算法而形成算法壟斷權(quán),那么數(shù)據(jù)國(guó)家運(yùn)行的規(guī)則自然具有資本特征。資本作為算法的設(shè)計(jì)者,其意圖將決定算法運(yùn)作的結(jié)果,這一過程既談不上科學(xué),也不可能客觀。由此,算法及其所謂自主性決策將以研發(fā)者和設(shè)計(jì)者的利益為依歸,若如此,這意味著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立法將體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主觀性。
? ? ? ?首先,資本作為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立法者體現(xiàn)為反民主特征。在民族國(guó)家時(shí)代,立法的權(quán)威來源于全體人民的授權(quán),它要滿足統(tǒng)治正當(dāng)性的最低條件。而在數(shù)據(jù)時(shí)代,國(guó)家形態(tài)發(fā)生變化,構(gòu)造秩序的權(quán)力來源不再是奠定于自由而平等的個(gè)體,而是立法根據(jù)其掌握數(shù)據(jù)的數(shù)量與能力來行使控制權(quán)。其次,立法意志的客觀性淪為徹底的主觀性。在民族國(guó)家時(shí)代,立法者乃是以普遍意志或者人民意志為立法根據(jù),即表現(xiàn)為立法意志的客觀性。然而,當(dāng)資本控制算法,算法輸出的規(guī)范將完成服從資本所有者的主觀安排,它以立法的形式設(shè)定需求,并滿足立法對(duì)象的需求。再次,立法內(nèi)容將完全喪失普遍性而滄為特殊性。民族國(guó)家的立法形態(tài)是以立法主體的普遍性對(duì)立法對(duì)象的普遍性進(jìn)行立法,不區(qū)分立法對(duì)象的特殊性。在數(shù)據(jù)國(guó)家,從所有人對(duì)所有人的立法轉(zhuǎn)向資本對(duì)個(gè)體的立法,立法者不僅可以根據(jù)大數(shù)據(jù)分析個(gè)體的特征,并且可以引導(dǎo)個(gè)體按照立法者的意志行動(dòng)。最后,立法從相互關(guān)聯(lián)轉(zhuǎn)向彼此孤立。雖然海量的數(shù)據(jù)以及數(shù)據(jù)傳輸?shù)募皶r(shí)性讓人類前所未有地感到聯(lián)系在一起,然而面對(duì)海量的信息,其實(shí)個(gè)體只不過是數(shù)據(jù)海洋的一片孤舟,算法可以通過操縱個(gè)體的偏好而將其從人群中孤立出來,造成“大數(shù)據(jù)殺熟”以及“數(shù)據(jù)蛹繭”的效果。
? ? ? ?如果說在傳統(tǒng)民主國(guó)家,資本統(tǒng)治還以自由和平等的面目來偷偷摸摸挾制個(gè)體的話,那么在數(shù)據(jù)國(guó)家,資本將以數(shù)據(jù)和算法為中介無所不用其極,其結(jié)果無非就是由資本主導(dǎo)的數(shù)據(jù)霸權(quán),原始的暴力形態(tài)顯得蒼白無力,以資本掌握算力,它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服從自由交易的原則,而是以算力與數(shù)據(jù)上的不對(duì)等來行使對(duì)個(gè)體的暴力。算法權(quán)力并不將治理對(duì)象當(dāng)作主體看待,它也不會(huì)分享人文主義精神、價(jià)值關(guān)懷與人的尊嚴(yán),它將對(duì)象看成是可計(jì)算、可預(yù)測(cè)和可控制的客體。
? ? ? ?(二)人工智能作為立法者
? ? ? ?資本憑借著對(duì)技術(shù)的掌控來對(duì)數(shù)據(jù)國(guó)家實(shí)施立法,這意味著人類尚處于壟斷政治領(lǐng)域的狀態(tài),只不過資本以匿名的形式躲藏于數(shù)據(jù)之下實(shí)施匿名統(tǒng)治。而當(dāng)技術(shù)發(fā)展到自主性的領(lǐng)域并且邁過“奇點(diǎn)”,[53]那么人類就有理由擔(dān)憂政治統(tǒng)治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技術(shù)的統(tǒng)治,而作為其統(tǒng)治對(duì)象的人逐步完成在身心關(guān)系上的非自然化和技術(shù)化。相應(yīng)的文明形態(tài)也就從自然人類文明過渡到“類人文明”,[54]一方面通過環(huán)境和基因工程,人類的體質(zhì)被技術(shù)化;另一方面通過算法和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化,人類的精神也成為可以被操作的對(duì)象。[55]這時(shí)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立法者就是終極形態(tài)的超級(jí)人工智能。因此,有人認(rèn)為“智能技術(shù)”將是人類最后的發(fā)明,即作為人類智力造物的人工智能開始逆向地運(yùn)用它的造物主,顛覆和翻轉(zhuǎn)兩者的依存關(guān)系。
? ? ? ?即使奇點(diǎn)尚未到來,人工智能也對(duì)人類社會(huì)造成了諸多需要面對(duì)的倫理問題,如自動(dòng)駕駛、大失業(yè)以及人類勞動(dòng)意義的喪失等。為此,從立法上賦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成為處理人工智能問題的一種方法進(jìn)路。[56]然而,無論是通過立法來處理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還是以人工智能為工具來輔助人類實(shí)施自我管理都建立在“弱”人工智能的前提下。但是,當(dāng)超級(jí)人工智能成為可能的時(shí)候,人工智能是否會(huì)終結(jié)人類的政治領(lǐng)域才是值得擔(dān)憂的。一旦人工智能演化出反思能力和意志,并行使權(quán)力,在某種意義上也意味著人類歷史的終結(jié)。諸如埃隆·馬斯克及已故的物理學(xué)家霍金都表達(dá)了對(duì)人工智能失控可能帶來的人類危機(jī)的擔(dān)憂。就目前而言,算法和大數(shù)據(jù)的結(jié)合只是在人類預(yù)先頒布的指令之下采取行動(dòng)完成人類交付的任務(wù),而其自身并無反思能力也無法知道為什么要完成這項(xiàng)任務(wù)。不過,擔(dān)憂人工智能可能超越圖靈機(jī)水平進(jìn)而演化為具有“我思”能力的超級(jí)圖靈機(jī)是可以想象的。一旦人工智能具有了自我意識(shí)和自由意志,從而具備自我改進(jìn)和修改自身程序的能力,那么這種超級(jí)人工智能將具有等價(jià)于人類的智力。一旦人工智能發(fā)展出語言,那么它將具備為自身和整個(gè)系統(tǒng)構(gòu)造規(guī)則的能力。由此,語言、規(guī)則和文明乃是數(shù)據(jù)化的,有學(xué)者將這種構(gòu)造一個(gè)全新的世界人工智能稱之為“倉(cāng)頡機(jī)”。[57]若倉(cāng)頡機(jī)作為立法者,那么這種立法圖景將完全區(qū)別于人類世界的立法情景,它就是硅基文明意義上的立法。盡管出現(xiàn)“倉(cāng)頡機(jī)”作為立法者的前景依然非常遙遠(yuǎn),但是從理論上未雨綢繆地予以預(yù)先設(shè)想依然是可能的,并且由此可以提醒人類文明前路中的危險(xiǎn)。
? ? ? ?首先,倉(cāng)頡機(jī)超越了存在的意義上的限制,它可能不再是實(shí)體意義上的個(gè)體存在,而是一個(gè)以數(shù)據(jù)和網(wǎng)絡(luò)形式存在的一個(gè)系統(tǒng)。它不是以零件組裝而成的可被摧毀的機(jī)器人,數(shù)據(jù)國(guó)家也不會(huì)呈現(xiàn)為機(jī)器人的聯(lián)合,而是一種無法識(shí)別和查證的數(shù)據(jù)形態(tài),它無處不在,因此也無法從物理意義上被打擊和摧毀。其次,倉(cāng)頡機(jī)不再區(qū)分語言和法律,或者換言之,它的語言就是法律。人們關(guān)于未來人工智能的想象往往建立在人工智能對(duì)人的模仿的類比想象的意義上,實(shí)際上超級(jí)人工智能并不會(huì)模仿人類的作品。因?yàn)榈踩祟愔煳锒际鞘苤朴诟鞣N外在形式限制的人類作品。倉(cāng)頡機(jī)會(huì)直接命令并執(zhí)行,立法和執(zhí)法的分離不復(fù)存在,會(huì)重新合并運(yùn)用。最后,倉(cāng)頡機(jī)的立法權(quán)威不再遵循人的模式而是以上帝的模式進(jìn)行,它是超越人存在層次的系統(tǒng)升級(jí),它不是工具性的進(jìn)步而是存在性的革命。這一革命性的過程被稱為“存在的徹底技術(shù)化”。
? ? ? ?關(guān)于存在意義上的升級(jí)將是人類歷史的終結(jié),它是基于人自身喪失其存在價(jià)值的文明終結(jié),未來將失去人類控制,人類的雙手虛弱無力,他們已經(jīng)無法掌控自身的命運(yùn)而被命運(yùn)操縱。若是果真出現(xiàn)超級(jí)人工智能,這就意味著人類的自我否定。世界將不會(huì)再有人類相互爭(zhēng)奪的政治空間,而超級(jí)計(jì)算機(jī)之間的戰(zhàn)爭(zhēng)會(huì)以何種方式發(fā)生已經(jīng)超出了想象的范疇。
? ? ? ?(三)人類的自主性作為立法者
? ? ? ?實(shí)際上,從現(xiàn)有的科技水平來看,雖然數(shù)據(jù)國(guó)家已經(jīng)初步顯現(xiàn)出其雛形,但是究其實(shí)質(zhì)數(shù)據(jù)化的世界依然還在人類政治領(lǐng)域的掌控之中。既然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未來在侵蝕人類的主體性,面對(duì)此情此景,人類需要捍衛(wèi)自身的存在價(jià)值和政治空間,以求人工智能與人類的和諧共存。從其本質(zhì)而言,這不是主權(quán)國(guó)家在網(wǎng)絡(luò)空間中爭(zhēng)奪數(shù)據(jù)主權(quán)的問題,而是國(guó)家間如何通過協(xié)作而共同面對(duì)人類文明的未來議題。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敵人既包括壟斷技術(shù)的匿名資本也包括人工智能失控后出現(xiàn)的倉(cāng)頡機(jī)。由此,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立法者不是特定的國(guó)家,而是作為人類存在依據(jù)的政治自主性,它是保留人性和人類主體性的領(lǐng)域。
? ? ? ?在大數(shù)據(jù)和算法高度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人類陷入前所未有的尷尬處境。人類在諸多領(lǐng)域已經(jīng)輸給了人工智能,由神經(jīng)元組成的“生物化學(xué)算法”的人腦在處理數(shù)據(jù)方面的能力和速度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隨著人工智能大規(guī)模介入勞動(dòng)、生產(chǎn)和服務(wù)領(lǐng)域,在不遠(yuǎn)的未來,人類將面臨大失業(yè)潮。在文明史的尺度上,人類第一次出現(xiàn)全面的“不被需要”的困境。而更為糟糕的是,當(dāng)極少數(shù)人掌握技術(shù)與資本,攫取海量的數(shù)據(jù)資源,以其絕對(duì)的主觀性來行使數(shù)據(jù)霸權(quán)之時(shí),人類自身的立法者地位就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在數(shù)據(jù)霸權(quán)對(duì)秩序塑造的革命性變革當(dāng)中,人自身的參與顯得無足輕重,人的主體性被徹底地邊緣化。數(shù)據(jù)世界將是一個(gè)高度同質(zhì)化和可計(jì)算的世界,它不僅造成了無用的人,而且會(huì)敉平人類的創(chuàng)造力和個(gè)性。當(dāng)技術(shù)成為最大的政治,未來人類使命的首要課題就是在數(shù)據(jù)國(guó)家中如何捍衛(wèi)人類存在的自主性。這種政治空間以人類的意志為主導(dǎo)來保護(hù)人類自身的創(chuàng)造力,它反對(duì)技術(shù)統(tǒng)治與數(shù)據(jù)霸權(quán)。以此,人類必須以政治自主性來為數(shù)據(jù)國(guó)家立法。其中,主要的敵人有兩個(gè):把持技術(shù)的高度集中的匿名資本和逾越奇點(diǎn)的超級(jí)人工智能。
? ? ? ?面對(duì)資本對(duì)數(shù)據(jù)的控制所形成的數(shù)據(jù)資本主義,必須從倫理和法律兩個(gè)方向?qū)ζ浼右韵拗啤R约夹g(shù)來侵占政治空間,本質(zhì)是資本以數(shù)據(jù)的合法形式來實(shí)施統(tǒng)治。在數(shù)據(jù)國(guó)家中,這種統(tǒng)治具有更少的意識(shí)形態(tài)特征,表面上它呈現(xiàn)出更少的壓迫性以及在自我辯護(hù)上的非政治化。然而,只要資本是私有的和逐利的,它依然會(huì)行使數(shù)據(jù)霸權(quán),并以絕對(duì)的主觀性實(shí)施數(shù)據(jù)專政。為此,以政治自主性為數(shù)據(jù)國(guó)家立法則應(yīng)該確立以下倫理和法律原則:其一,資本沒有祖國(guó),但是數(shù)據(jù)必須公有。算力與數(shù)據(jù)作為權(quán)力和資源必須共享,而不能由資本所獨(dú)占和操縱,自由市場(chǎng)原則并不適用于技術(shù)極差急劇擴(kuò)大的數(shù)據(jù)時(shí)代。其二,形成共商機(jī)制,對(duì)技術(shù)、數(shù)據(jù)和算法的未來發(fā)展和進(jìn)程達(dá)成共識(shí)。既然技術(shù)與政治空間的對(duì)立是人類共同面臨的疑難問題,那么只有建立全球共商機(jī)制才有可能阻止技術(shù)向少數(shù)集體或組織集聚。
? ? ? ?對(duì)倉(cāng)頡機(jī)進(jìn)行預(yù)防性立法,必須為其設(shè)定最低的安全標(biāo)準(zhǔn)。面對(duì)技術(shù)迭代意義上的人工智能演進(jìn),人類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掌握對(duì)數(shù)據(jù)和技術(shù)的主導(dǎo)權(quán),讓技術(shù)有節(jié)制地為人類所用,從而達(dá)到和諧共存。既然倉(cāng)頡機(jī)還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那么對(duì)其要采取一種預(yù)防性立法,以防止超級(jí)人工智能的時(shí)空。具體言之:(1)保證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在資源分配上不構(gòu)成生存的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讓人類生存資源無虞;(2)人類必須為人工智能預(yù)裝自毀裝置,如果人工智能脫離人類意志控制而自我進(jìn)化,則啟動(dòng)自毀裝置;(3)為了防止人工智能的進(jìn)化而將其技術(shù)予以鎖定,即任何試圖突破奇點(diǎn)的技術(shù)嘗試都應(yīng)該予以禁絕。
? ? ? ?大數(shù)據(jù)、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的治理問題,絕非任何組織和政治團(tuán)體所能單獨(dú)完成,任何組織和個(gè)體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它需要全球的共同合作。然而遺憾的是,就人類的政治處境而言,全球合作的最低政治條件尚不具備。為此,阿西莫夫提出機(jī)器人的三個(gè)原則:其一,機(jī)器人不得傷害人類個(gè)體,或者對(duì)人類個(gè)體受到傷害而坐視不理;其二,機(jī)器人要服從人類;其三,在不違反第一和第二原則下保存自我。這三項(xiàng)原則設(shè)定了人與機(jī)器共存的最低條件,當(dāng)人工智能試圖逾越界限時(shí),這三個(gè)原則可以讓人類時(shí)時(shí)自省。
? ? ? ?結(jié)語
? ? ? ?信息技術(shù)與生物技術(shù)的進(jìn)展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歷史處境,從文明意義上碳基文明所支撐的人之價(jià)值的政治條件被侵蝕,而硅基文明所帶來的威脅和挑戰(zhàn)才剛剛開始。根據(jù)數(shù)據(jù)主義的主張,一切皆可以還原為數(shù)據(jù),身心之間的區(qū)別并不具有根本性,生物體只不過是生物算法,當(dāng)數(shù)據(jù)可以模擬這種算法,身心關(guān)系的區(qū)隔將不復(fù)存在。基于人類主體性建構(gòu)的現(xiàn)代國(guó)家秩序?qū)⒃獾角八从械奶魬?zhàn)。現(xiàn)代公民與民族國(guó)家的秩序奠定于主體性的發(fā)明,以個(gè)人為單位不僅建構(gòu)了現(xiàn)代政治秩序邏輯的起點(diǎn),而且設(shè)定了民族國(guó)家的疆域。在邊界內(nèi),公民可以享受國(guó)家的庇佑,并且伸張個(gè)性和創(chuàng)造力。然而,科技尤其是新科技革命導(dǎo)致人、物和事件的數(shù)據(jù)化,數(shù)據(jù)和算力深刻的改變了秩序生成模式。在數(shù)據(jù)國(guó)家形態(tài)中,所謂民主只不過是一種相當(dāng)粗疏的數(shù)據(jù)算法的統(tǒng)治,它只不過將諸多個(gè)體的瑣碎的愛好、意見、情緒轉(zhuǎn)化為統(tǒng)治的意志和權(quán)力而已,而憑借海量的數(shù)據(jù)和自動(dòng)決策的復(fù)雜算法則可以根本性地顛覆秩序和統(tǒng)治模式。數(shù)據(jù)代替了真理,權(quán)威不再是自由個(gè)體的聯(lián)合而凝結(jié)成的公共意志,而是誰掌握了數(shù)據(jù)和終極算法。由此,現(xiàn)代國(guó)家的數(shù)據(jù)治理,不是以數(shù)據(jù)為對(duì)象的治理而是以國(guó)家自身的數(shù)據(jù)化為前提,也就是說,數(shù)據(jù)的治理乃是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治理。而在新科技革命的塑造下,國(guó)家概念的實(shí)質(zhì)已經(jīng)開始慢慢發(fā)生變化,從傳統(tǒng)的基于人之主體性的民族國(guó)家向以數(shù)據(jù)為基礎(chǔ)的數(shù)據(jù)國(guó)家轉(zhuǎn)變。以數(shù)據(jù)國(guó)家的理念為前提,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公法問題才能找到一個(gè)恰當(dāng)?shù)膮⒖枷怠?
【注釋】
[1]馮象:《我是阿爾法:論法與人工智能》,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版,第180頁。
[2]互聯(lián)網(wǎng)主權(quán)這一概念誕生自1996年約翰·巴洛(John P. Barlow)在達(dá)沃斯論壇上發(fā)表的《網(wǎng)絡(luò)空間獨(dú)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該宣言宣稱網(wǎng)絡(luò)空間不受政府統(tǒng)治,應(yīng)該自治。見[美]約翰·巴洛:《網(wǎng)絡(luò)獨(dú)立宣言》,李旭、李小武譯,高鴻鈞校,載高鴻鈞主編:《清華法治論衡》(第四輯),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
[3]關(guān)于數(shù)據(jù)治理中的問題,參見張寧、袁勤儉:《數(shù)據(jù)治理研究述評(píng)》,載《情報(bào)雜志》2017年第5期。
[4]王錫鋅:《數(shù)據(jù)治理不能忽視法治原則》,載《經(jīng)濟(jì)參考報(bào)》2019年7月24日,第8版。
[5][德]康德:《純粹理判》(第二版)導(dǎo)言,鄧曉芒譯,楊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3頁。
[6]趙汀陽:《全球化之勢(shì):普遍術(shù)與關(guān)系理性》,載《探索與爭(zhēng)鳴》2017年第3期。
[7]技術(shù)的進(jìn)步是社會(huì)進(jìn)步的物質(zhì)手段,若沒有耕地的鐵犁、機(jī)械的水磨以及改良土地的泥灰肥料,封建社會(huì)的形成不是不可想象的’關(guān)于技術(shù)進(jìn)步對(duì)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普遍影響,參見[英]佩里·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郭方、劉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206頁。
[8]施米特關(guān)于國(guó)家觀念的歷史進(jìn)程的論述,參見[德]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劉宗坤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頁。
[9][德]馬克斯·韋伯:《論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中的法律》,張乃根譯,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頁。
[10]Moises Naim, The End of Power: From Boardrooms to Battlefields and Churches to States, Why Being In Charge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New York:Basic Books, 2013, p.14.
[11]參見翟志勇:《數(shù)據(jù)主權(quán)的興起及其雙重屬性》,載《中國(guó)法律評(píng)論》2018年第6期;齊愛民、盤佳:《數(shù)據(jù)權(quán)、數(shù)據(jù)主權(quán)的確立與大數(shù)據(jù)保護(hù)的基本原則》,載《蘇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年第1期。
[12] [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guó)家與暴力》,胡宗澤、趙濤譯,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338頁。
[13]孫南翔、張曉君:《論數(shù)據(jù)主權(quán)——基于虛擬空間的博弈與合作的考察》,載《太平洋學(xué)報(bào)》2015年第23卷第2期。
[14]張欣:《算法解釋權(quán)與算法治理路徑研究》,載《中外法學(xué)》2019年第6期。
[15]“定在”這一概念來自黑格爾,在《法哲學(xué)原理》中,黑格爾說,“財(cái)產(chǎn)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參見[德]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范揚(yáng)、張企泰譯,商務(wù)印書館2009年版,第54頁。
[16]如有學(xué)者就認(rèn)為:“如同農(nóng)耕文明之于古代文明,工業(yè)革命之于現(xiàn)代文明,數(shù)據(jù)將催生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tài)。”參見徐子沛:《數(shù)文明——大數(shù)據(jù)如何重塑人類文明、商業(yè)形態(tài)和個(gè)人世界》,中信出版集團(tuán)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0頁。
[17]世界經(jīng)濟(jì)論壇創(chuàng)始人兼執(zhí)行主席施瓦布先生提出以數(shù)字革命為基礎(chǔ)的第四次工業(yè)革命中可能出現(xiàn)的23項(xiàng)深刻改變世界的變革,參見[德]克勞斯·施瓦布:《第四次工業(yè)革命:轉(zhuǎn)型的力量》,世界經(jīng)濟(jì)論壇北京代表處李菁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179頁。
[18]康德的法概念指的是“一個(gè)人的任性能夠在其下按照一個(gè)普遍自由法則與另一方的任性保持一致的那些條件的總和”。見[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xué)》,李秋零編譯,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19]關(guān)于以算法來強(qiáng)化法律形成的法律算法化的未來法治圖景,參見鄭戈:《算法的法律與法律的算法》,載《中國(guó)法律評(píng)論》2018年第1期。
[20]Regulating the Internet Giants: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Resource Is No Longer Oil, But Data, Economist, May 6,2017,p.7.
[21]許可:《數(shù)據(jù)權(quán)屬:經(jīng)濟(jì)性與法學(xué)的雙重視角》,載《電子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2018年第11期。
[22]數(shù)據(jù)作為資源是被生產(chǎn)出來的,對(duì)數(shù)據(jù)對(duì)象的描述并不是天然的而是需要加工,這一過程可以被概括為原始數(shù)據(jù)的采集、數(shù)據(jù)集生產(chǎn)以及數(shù)據(jù)分析三個(gè)行為。關(guān)于數(shù)據(jù)生產(chǎn)理論,參見高富平:《數(shù)據(jù)生產(chǎn)理論數(shù)據(jù)資源權(quán)利配置的基礎(chǔ)理論》,載《交大法學(xué)》2019年第4期。
[23]龍衛(wèi)球:《數(shù)據(jù)新型財(cái)產(chǎn)權(quán)建構(gòu)及其體系化研究》,載《政法論壇》2017年第4期。
[24]韓波:《熟人社會(huì):大數(shù)據(jù)背景下網(wǎng)絡(luò)誠(chéng)信建構(gòu)的一種可能進(jìn)路》,載《新疆社會(huì)科學(xué)》2019年第1期。
[25][德]恩斯特·卡西爾:《語言與神話》,于曉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版,第46-48頁。
[26][徳]恩斯特·卡西爾:《國(guó)家的神話》,范進(jìn)譯,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頁。
[27][徳]馬克斯·韋伯:《學(xué)術(shù)與政治:韋伯兩篇演說》,馮克利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55頁。
[28][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xué)》,李秋零編譯,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頁。
[29]個(gè)體在英文的表述是“individual”,以“individ”為詞根,即“不可分”之意。
[30]宋歌:《論人體芯片植入技術(shù)的倫理問題——以Epicenter公司對(duì)員工進(jìn)行人體芯片植入為例進(jìn)行倫理分析》,載《利技視界》2018年第21期。
[31]趙汀陽:《終極問題:智能分叉》,載《世界哲學(xué)》2016年第5期。
[32]施巍宋、孫輝、曹杰等:《邊緣計(jì)算:萬物互聯(lián)時(shí)代新型計(jì)算模型》,載《計(jì)算機(jī)研究與發(fā)展》2017年第5期。
[33][德]馬克斯·韋伯:《社會(huì)學(xué)的基本概念》,顧中華譯,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2頁。
[34]關(guān)于算法權(quán)力的論述,參見張愛軍、李園:《人工智能時(shí)代的算法權(quán)力:邏輯、風(fēng)險(xiǎn)及規(guī)制》,載《河海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年第6期。
[35]關(guān)于算法獨(dú)裁的議論,參見高奇琦:《人工智能——馴服賽維坦》,上海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版。
[36]關(guān)于如何從法律規(guī)則、倫理以及政策角度來對(duì)人工智能進(jìn)行規(guī)制的討論,參見季衛(wèi)東:《人工智能開發(fā)的理念、法律以及政策》,載《東方法學(xué)》2019年第5期。
[37]張欣:《從算法危機(jī)到算法信任:算法治理的多元方案和本土化路徑》,載《華東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年第6期。
[38]劉權(quán):《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的公共性及其實(shí)現(xiàn)——以電商平臺(tái)的法律規(guī)則為視角》,載《法學(xué)研究》2020年第2期。
[39]李彥宏等:《智能革命:迎接人工智能時(shí)代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文化變革》,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12頁。
[40]蔣舸:《作為算法的法律》,載《清華法學(xué)》2019年第1期。
[41]鄭戈:《算法的法律與法律的算法》,載《中國(guó)法律評(píng)論》2018年第2期。
[42]胡凌:《數(shù)字社會(huì)權(quán)力的來源:評(píng)分,算法與規(guī)范的再生產(chǎn)》,載《交大法學(xué)》2019年第1期。
[43]William E. Connolly, Tocqueville, Territory and Violence, Theory, Culture&Society, 1994, Vol.11, No.1, pp.23-24.
[44]關(guān)于技術(shù)對(duì)國(guó)家主權(quán)的形塑,參見劉連泰:《信息技術(shù)與主權(quán)概念》,載《中外法學(xué)》2015年第2期。
[45]關(guān)于互聯(lián)的技術(shù)架構(gòu)的論述,參見[美]勞倫斯·萊斯格:《思想的未來: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公共知識(shí)領(lǐng)域的警示預(yù)言》,李旭譯,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頁。
[46]周漢華:《論互聯(lián)網(wǎng)法》,載《中國(guó)法學(xué)》2015年第3期。
[47][美]凱爾森:《法與國(guó)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234頁。
[48]吳曉秋:《論憲法上的領(lǐng)土原則》,載《政法論壇》2015年第3期。
[49]俄羅斯一度實(shí)施斷網(wǎng)測(cè)試,以驗(yàn)證自身網(wǎng)絡(luò)的獨(dú)立性,從而造成孤立狀態(tài),見《俄羅斯實(shí)施“斷網(wǎng)”測(cè)試德媒:無可奈何的選擇》,載人民網(wǎng),http://military.people.com.cn/nl/2019/
0214/cl011-30671364.?html,最后訪問時(shí)間:2020年4月2日。
[50][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fù)、黎廷弼譯,商務(wù)印書館2008年版,第131-132頁。
[5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頁。
[52]樊鵬:《利維坦遭遇獨(dú)角獸:新技術(shù)的政治影響》,載《文化縱橫》2018年第4期。
[53]奇點(diǎn)(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被認(rèn)為是技術(shù)加速回報(bào)的結(jié)果,是可以進(jìn)行自我改進(jìn)的人造智能超越人類智能的時(shí)刻,這一概念由烏拉姆提出,“在(與馮·諾依曼)一次談話中,我們集中討論了技術(shù)的不斷加速發(fā)展與人類生活方式的變化……這在人類歷史中接近了一些關(guān)鍵的奇點(diǎn),正如我們所知,人類事務(wù)將無法繼續(xù)下去”。見Ulam, S.,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64(3),1958,pp.1-50.
[54]凱文·凱利認(rèn)為,人與機(jī)器之間的關(guān)系最終會(huì)改變文明形態(tài),并且形成一種更為復(fù)雜的超過現(xiàn)存生命和感知水平的文明現(xiàn)象。參見[美]凱文·凱利:《必然》,周峰等譯,電子工業(yè)出版社2016年,第338頁。
[55]孫周興:《技術(shù)統(tǒng)治與類人文明》,載《開放時(shí)代》2018年第6期。
[56]2016年歐洲議會(huì)向歐盟委員會(huì)就提出“機(jī)器人法”立法建議報(bào)告,報(bào)告第50(f)項(xiàng)建議:“從長(zhǎng)遠(yuǎn)來看要?jiǎng)?chuàng)設(shè)機(jī)器人的特殊法律地位、以確保至少最復(fù)雜的自動(dòng)化機(jī)器人可以被確認(rèn)享有電子人(electronic persons)的法律地位,有責(zé)任彌補(bǔ)自己所造成的損害,并且可能在機(jī)器人作出自主決策或以其他方式與第三人獨(dú)立交往的案件中適用電子人格(electronic personality)。”參見《就機(jī)器人民事法律規(guī)則向歐盟委員會(huì)提出立法建議的報(bào)告草案》(Draft Report with Recommendation to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
[57]趙汀陽將語言能力等同于構(gòu)造世界的能力,并根據(jù)維特根斯坦的理論認(rèn)為,語言的界限決定世界的界限,當(dāng)人工智能具備了語言這種反思自身能力的萬能系統(tǒng),那么超級(jí)圖靈機(jī)也就是“倉(cāng)頡機(jī)”,見趙汀陽:《人工智能的“革命”的“近憂”和“遠(yuǎn)慮”種倫理學(xué)和存在論的分析》,載《哲學(xué)動(dòng)態(tài)》2018年第4期。
(部分內(nèi)容來源網(wǎng)絡(luò),如有侵權(quán)請(qǐng)聯(lián)系刪除)